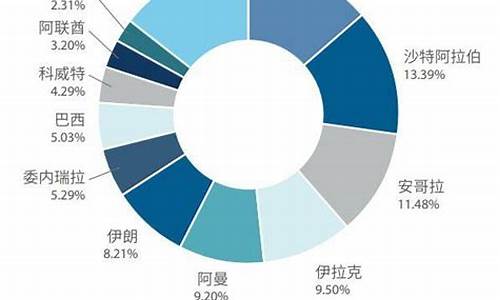小驴拉磨香油价格_河南省小驴拉磨商贸有限公司
1.三位亲人的悲苦人生
三位亲人的悲苦人生

十多天来,老人坟头枯黄的野草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情景,一直浮现在眼前。
几天来,不知道怎么了,难以名状的不安与心痛.,从未有过的酸楚与压抑让自已透不过气来。此刻的我真的不知 ‘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,来缓解心中的那份连自已都表达不清楚的感觉:是思念,是为她们悲凉、凄苦的人生而心痛,还是自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脆弱!唉,苍桑岁月,已是那么的久远,为什么还会有这般心绪!没办法,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排解吧!
奶奶,一个虽未谋面,但在我心中是那么清晰而纯粹的女人。
奶奶离世已经多年了,那时父亲才七八岁,关于奶奶的事是母亲听三大娘讲的,三大娘和奶奶年龄相仿。小时候,我总是想从母亲那里听到有关奶奶的事。
那是民国时期,不满17岁的奶奶因为家里多穷的揭不开锅,被父母逼着嫁给了一个带着两个儿子的爷爷。爷爷人高马大,家里有几亩荒地,能让奶奶吃上一顿饱饭。接奶奶那天,是冬至,天空还飘着雪花,特别阴冷,一大早,家族里的两个长辈和三大娘就出发了,她们推着独轮车,牵一头小毛驴,独轮车上放着一个印花包袱,里面是接亲的棉袄、棉裤,和一双棉鞋。小毛驴身上驮着一布袋麦子,和半布袋高梁,半布袋黄豆。就为了这点粮食,奶奶的父母就这样把一个性格柔弱,温顺善良的,不满17岁的女儿给“卖”了,卖给了一个大儿子和她女儿差不多大的,比小儿子大不了几岁的爷爷。唉!也许是在那样的寒冬,独轮车上的那点粮食能让一家人度过难熬的冬天吧!
奶奶就这样“娶”过来了。迎进屋里的奶奶,茶饭未进一口,畏畏缩缩,手足无措,在炕沿上坐了整整一天。
爷爷的家,堂屋是上面铺着茅草和麦杆两搭土坯房,偏房是用几根柱子支起来的茅草棚,四周用高粱杆乱树枝绑在一起,糊了一层泥巴的围墙。这偏房既是灶屋,也是磨房,北墙边,给小毛驴支了一口木槽。爷爷家的光景也就是靠着河边的荒地和一盘石磨过生活。
冬至过后,也是奶奶刚过门没几天,夜晚狂风挟着鹅毛般的雪花铺天盖地,尖叫的风吼了一夜。天没亮奶奶就起了床去灶屋给牲口加草料,加好草料又拿起铁铣去铲那没漆的积雪,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把堂屋和灶屋之间铲出了一条路。之后又去收拾牲口铺,清理驴粪尿,给驴铺铺垫草木灰。这前前后后忙了一大阵子,她气都没有喘一口,就放下铁铣又拎起木桶,去村口的老井提水,在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着,好不容易提进灶屋,水,也只剩下半桶。天已经大亮了,坐在灶火旁烧锅的奶奶,呆呆地看着灶膛里的火苗……
嘶叫的狂风也没能叫起来那个和父亲年龄一样大的男人,更别说指望那两个和自已差不多大的“儿子”!“唉,此时的奶奶也是欲哭无泪吧!”
说话间,到了腊月初八,俗话说,“吃了腊八饭,就把年来办”。过了腊八,不论穷富,都要磨面,高粱面,小麦面,红薯干面都要磨一些。每年一到这几天,灶屋里的这盘磨也就不得闲了,上午东家磨,下午西家磨,有时候能磨到半夜。奶奶也只能趁左邻右舍的空磨面了,好者有小毛驴,不像邻居们那样去推磨。那天,快到二更天了,奶奶把粮食放到磨台旁,准备磨面,那个邋里邋遢能叫“爹”的人,只是把帮着把驴套上磨,便腆着脸和他那两个儿子比着缩进了被窝。奶奶,一个少言寡语,只会干活的人,自已忙到天亮。
每逢年关,是这个家“丰收”时候,村子里每家磨完面后都要留下一瓢麸皮,再加上压磨的麸皮,驮到集上,能换回年货来。
蒸年下馍了,奶奶在灶屋忙了一天,杂粮馍,好面馍,堆了满满一锅盖。第二天爷爷牵着毛驴驮了小半布袋好面,一斤香油,一小竹篮馍送给了奶奶娘家。“这也许是爷爷这辈子做的能对得起奶奶的一件事吧”。第二年,麦收过后,奶奶病倒了,爷爷以活忙为由,把她送回了娘家,打那天起,这边的大人小孩没有看望过。
在娘家的几个月,奶奶的病渐渐的好了,到了秋收时节,爷爷来接奶奶回去收秋,一向温顺的奶奶再也不愿回那个家了。又隔几日,爷爷叫上三大娘带着小儿子又一次上奶奶的娘家,叫小儿子下跪,再加上三大娘苦苦相劝,心软的奶奶还是无奈的回来了。几年间,奶奶像牲口一样,家里地里,没明没夜的干。卖了能帮力耕地,拉磨的驴,给和自已差不多大的“大儿子”娶妻生子;拉土和泥,脱土坯又盖了两间偏房,给“小儿子”娶了媳妇;自已也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几年间既要养活年幼的孩子,又要照顾生病的爷爷。(事实上,小儿子的两个儿子的年龄比父亲还要一两岁,大儿子的孩子更大)“这里有多少辛酸,多少苦难,只有奶奶一人知道”。
父亲四岁那年,爷爷死了。
堂屋几年前分家时给大儿子,小儿媳刁钻刻薄,偏房也给了他们,奶奶和父亲姑姑,住在丁灶屋拴驴的牲口铺上。强悍的小儿媳妇还时常的去她们屋偷东拿西。河坡里那二亩多多荒地,只给奶奶留了三分,为了节省粮食,奶奶总是在春夏时节,挖各种野菜,晒干,掺些麸皮,蒸菜团子养活姑和父亲,父亲年幼,实在没办法时,奶奶去扫些墙上的“飞箩面”来给她们熬点稀饭送那咽不下去的菜团。
祖祖辈辈生活在小河湾里的村庄,不是发水就是闹灾荒,那年7月一场大雨,河水泛滥,淹没了所有的庄稼,仅靠三分地收的那点粮食,让奶奶雪上加霜,也得亏了那些干野菜,让她们熬过了这漫长的严冬。也正是这些野干菜,让奶奶熬一年又一年。第二年麦黄了,.眼看就有盼头了,可父亲和姑姑因常常吃野菜,肚子胀鼓鼓的躺床上奄奄一息。想给他们弄点麦仁做点面粥吧,可自家地里的那点庄稼还没有泛黄的迹象,焦虑不安的她想起村里的那大户人家。犹豫了半宿,没等天亮,奶奶走进那家的麦地。
正当她用镰刀割下第一把麦头的时候,忽然听到:“天明了去我家给孩子弄点面贴补一下吧”!听声音是村东头那瓦房院里的大爷,奶奶暗想,“走错麦地了!原来这是村东头瓦房院里的大爷,奶奶常常给他家帮工,虽是富人家,但很和善,时常的接济自已,人家待你不赖,还去‘偷’人家”…...此时的奶奶已无地自容。那件事过后,奶奶总觉得对不住人家,窝气在心,一病不起,撇下了姑姑和7岁的父亲离开了人世。
村南面,多了一座孤苦伶仃的坟,村口多了一个常常是泪眼朦眬的孤儿。
奶奶离世时三十来岁,但在我心中永远“存留着一个善良、慈祥的老人形象。
至今,我对爷爷还是特别的怨恨。
三大爷和父亲是堂兄弟,奶奶走后,三大爷让父亲去他家吃饭,三大娘托人把十二岁的姑送到别村当童养媳。当时,那家的儿子还在上学,说是童养媳不如说是使唤丫头,天天干了家里干地里,有时稍不留心,她那个婆婆不管是扫帚,还是擀面杖,得着什么是什么就往身上打。十七岁那年,姑和她那儿子圆了房,随着儿子的降生,日子也好过了些。可好景不长,儿子半岁时染上了水痘死了。本来就嫌弃姑姑的婆婆,这下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,整天骂来骂去。姑的性情随奶奶,只会埋头干活,那与生俱来的倔强、忍耐,让她无论受怎样的辱骂,都不言语,不流泪。但姑姑为在战场上不知是生是死的十五岁的父亲,常常暗自流泪。一边承受着来自对父亲生死未知的恐惧,一边承受着婆婆那终日无休止的辱骂,她苦苦地支撑着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表姐的出生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运,反而让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
大概是五四年,暂且叫姑父吧,可能是因为有文化,参加了工作。他上班不到两年,他母亲就闹着让离婚,说是姑鬓角上长了“鬓花”是妨人的命,不能给她们家续香火等。那个耳根子软的乡干部,劝着姑姑离婚不离家,把婚离了。最可恨的是还不让表姐跟着她母亲。时间不长,他领回一个扎着长辫子,能说会道的女人。姑姑为了表姐不受罪,住他们家院里西南角的一小间土坯房子里,姑姑在那小土坯房里度过了大半生。还养大了他们俩生的傻儿子。
长年累月的精神折磨,无法排解的心里压抑,让姑姑整天恍恍惚惚,见谁就说要害她,最后在痛苦中死去。姑姑没能进他们家的坟地,在他们村的西北方向,留下了一座孤单的坟……
我对姥的记忆,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,那时姥姥独身一人。她家离我家很近,有一里路的样子,姥姥常来我家,每次来总是从布衫大襟的里兜,掏出吃的给我们,至于是什么吃的已模糊不清了。记忆最深的,也是每每想起让我难受的,是姥姥每次来我家,不管是什么时间,十有八九是在母亲的大声斥责中而离去。很多次已是临近中午,斥责过后的母亲从未留过姥姥吃过午饭再走,过后,我的这个母亲也从来没有后悔过!在姥姥往外走的那一刻,不知为什么,我也总是呆呆地看着她一步一步蹒跚着离开家门,也没有上前去拉着她不让她走。
姥姥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人,从来没有见她大声地说过一句话,更没有见她发过脾气。到现在也理解不了,我那个脾气暴躁的娘,怎么能那样的糊涂,那样的不通情理!父亲常常无奈的说她,“找不着她恁糊涂的人”。
姥姥住的小屋时常会在我记忆中出现,很清晰。村子前面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,窄小的空间里,一张床,一个不大的锅台,一盏油灯摆放在锅台上方的搁板上。门后面用土坯支一块木板就算是擀面用的小案板,床头的另一侧的墙角有一个用麦秸编的盛粮食的屯子,再也没其它的家当。
那个年代,在乡下没男孩的都叫“绝户头”,是没人瞧得起的,姥姥有四个女儿,因为穷都远嫁他乡,一年半载也不曾回来。三女儿十几岁送到几百里之外的南乡,(那时靠两条腿走路,真的是很远了。)因为生姥姥的气三姨十几年赌气不回。五九年大集体,大锅饭,姥姥,姥爷两人的日子实在难熬,姥爷一路要饭去三女儿家,没想到会死到了南乡。年景好了以后,父亲去哪里用肩背,背回了姥爷的尸骨!
改革开放后,年近70的姥姥还得自已种地。一个小脚老人,刨红薯,背红薯的情景让我辛酸……
我上高中那一年,72岁的姥姥患偏瘫走完了她悲凉、凄苦的一生。
我的亲人们,愿你们在另一个世界,永远安好!!
[免责声明]本文来源于网络,不代表本站立场,如转载内容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联系邮箱:83115484@qq.com,我们会予以删除相关文章,保证您的权利。